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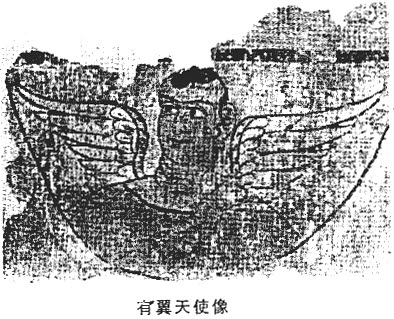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本文对新疆米兰遗址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画的题材、风格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在对中外学者不同学术观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有翼天使”壁画是佛教题材,但它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这证明文化交流是双向和有取舍的。
【关 键 词】佛寺遗址/壁画/题材/风格
斯坦因由于20世纪初在新疆的考察发掘,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同时,也在考古史上引起了一桩桩公案,被中外人士议论了近一个世纪。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桩有关学术观点的“公案”,因而值得学界格外关注。
1906年12月,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第二次来新疆考察。在若羌县东北部约50公里的磨朗遗址(即今称米兰遗址),他从一座塌毁的佛塔环行过道护壁上发现了一批有翼人物半身画像,另外的佛塔也有带翅的人物画像,但都已破碎。最后将七幅较完整的被斯坦因称为“有翼天使”的画像带走,现存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1921年斯坦因在考察报告中刊布了这些“有翼天使”壁画图,还在他1932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一书中说,从这些“有翼天使”的希腊式佛教造像的形式来看,“磨朗护墙板上这些画像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翼的爱罗神为其直接的祖先。”他不仅认为这些“有翼天使”是从希腊神话里爱罗神演变而来,而且还认为是“借自基督教造像”。后来,斯坦因又将“有翼天使”与佛教中的护法神“乾婆”联系起来进行考证。(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第85—86页。)
1932年,我国学者黄文弼考察了米兰,他在1948年发表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对斯坦因关于“有翼天使”与印度佛教中飞天的联系提出质疑。
1962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在《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一文中指出:“如果要追溯这些有翼神像的来源,与其说是渊源于希腊,还不如说是渊源于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很难想象,在佛教的支提窟中,有希腊神话上的‘爱罗神’画像。”从而认为斯坦因“强拉西方的古代神话于佛教艺术题材中,以致混淆了许多人的观念。”是“由于他们抱有偏见。”(注:《现代佛学》1962年第5期。)

1989年秋天,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考察米兰佛寺时,又发现了两幅并列的“有翼天使”画像。其位置也在佛塔回廊的护壁上,画像风格与斯坦因发现之“有翼天使”大致相同。这两幅画像的发现,又激发起人们对“有翼天使”问题的兴趣,相继的一些学者发表与斯坦因迥异的学术观点。霍旭初、赵莉的《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兼谈鄯善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注: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与此同时,从本世纪初至今,也有不少中外学者赞同斯坦因的学术观点,对他所作“有翼天使”的解释给予肯定,并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对其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关于“有翼天使”及斯坦因在米兰等地发现的绘画、雕塑作品的讨论,对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及与此相关的西域绿洲文化的渊源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助益于相关问题的澄清,有必要在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
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岁末,斯坦因在米兰进行发掘。他随手就发现了佛寺中废弃的具有希腊艺术风格的佛像雕塑,只不过这巨大的泥塑佛陀早已身首异处。最使他惊喜的是,在一座塌毁的窣堵波(佛塔)基座圆形走廊的护壁上,露出精美的“有翼天使”绘画,他禁不住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发问:“在亚洲腹部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泊岸上,我怎么能够看到这种古典式的天使呢?”他非常兴奋,来不及使用工具,仅“用光手”逐一清理,仔细观察,就立刻感觉到在昆仓山南北各处所看到的美术作品中,“这些壁画的构图和色调最接近古典的作风,完全睁开的大眼灵活地注视,小小微敛的唇部的表情,把我的心情引回到埃及托勒美同罗马时期木那伊墓中所得画版上绘的希腊少女以及青年美丽头部上去了。”(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第83页。)
在斯坦因看来,这些“有翼天使”不仅有明显的希腊古典风格,而且还是“借自基督教的造像”。经过比较考证,斯坦因将米兰废弃的时间,确定在尼雅遗址同时的“公元三世纪终了或其后不久”。(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第84页。)
米兰佛寺保存的所有绘画,表现的都是佛教故事,对此斯坦因很肯定,因为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绘画,如佛和六位弟子图。可是从其构图和色调来看,虽然题材是佛教的,但“美术表现的细微处却全是得之于希腊的模型”。例如佛和六弟子大而直的眼睛,同中亚一带绘画中长而歪斜的眼睛不同。还有衣褶样式以及手从袈裟里伸出来作曲指姿式等。在绘画技术上,表现肌肉时利用光与影这种希腊古典美术通常的画法。
七幅“有翼天使”绘画,外表有一种“天国博爱的和谐力量,面部表现有种强烈的个性”。关于“有翼天使”护壁板位于过道墙壁稍下部分的问题,斯坦因认为其“地位合适,天使扬起的注视,与绕塔右旋的信徒的眼光恰好相对。”(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第85页。)因为这些“有翼天使”的造像形式是“希腊式佛教美术”,所以斯坦因认为必须追溯到希腊神话,并应“以有翼的爱罗神为其直接的祖先”。同时他也承认,因经过中间的过程,当然也受有东方观念的影响。但他还是认定,这些“有翼天使”画像与古基督教派中的天使有一种亲属关系。这些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罗神成为米兰“有翼天使”画像的原因,斯坦因认为是不难解释的。因为犍陀罗派希腊式佛教画像是从有翼的爱罗神“抄袭”来的,用在佛教中代表印度传说中的乾达婆之类的飞天。他还说,你在米兰寺院看见这些如同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波斯西部见到的有翼画像,如果你仔细询问该寺院的守者,斯坦因断言“守者一定能立刻告诉你那些是犍(乾)达婆像。”
斯坦因发现的绘画,还有一幅是持花的浦蒂和一些青年人的像。“他们的希腊式面容似乎还杂有其他不易忘记的地中海东部或塞卡奥式的美,而精致的首饰又显示出近东或者伊兰的风味。”这些头部姿式十分像罗马人的青年,使人观之如同置身于“叙利亚或者罗马帝国东方诸省的一些别墅遗址之中,不是置身于中国境内的佛教寺院。”(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第87—88页。)斯坦因甚至猜测,“有翼天使”画像与上述相关的一些绘画,可能出于一位画家之手。因为所有这些绘画,采用的是希腊式佛教美术相同的一种传统表现方法。特别是在一幅白象图的绘画中,于白象身上有一段佉卢文的题记,其中有画家Tita(提塔)的署名,很可能是罗马人名Titas(提塔斯)的随俗语变化了的对应译名。(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第88—89页。)
总之,斯坦因把在米兰发现的“有翼天使”和同时出土的一些绘画,论证为希腊罗马风格,认为完全是受西方艺术影响的产物。

二
对斯坦因关于“有翼天使”的说法,最早提出异议的是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他说:“按斯坦因发见天使之位置,或在墙之下部护壁上,或在过道与供养人同样位置,是与佛教中位置飞天习惯不同。盖普通飞天,均在佛像后面背光上,作飞舞翱翔之姿态,手中或承日月、宝珠或持乐器,均不见有翼。……是着翼人像,为另一来源,与印度佛教中之飞天,毫无关系。”(注:《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烈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54页。)
阎文儒教授对斯坦因之批驳,最为激烈也比较具体。他首先提出断代问题,斯坦因从吐蕃时期城堡遗址发现大批8—9世纪的吐蕃文书,而发现“有翼天使”的废塔事实上是用土堆起的小支提窟,这种形制应该是10世纪之物。从有翼神像及佛同六弟子像的画风运笔看,已不是晋、南北朝“紧劲连绵”、“风趋电疾”、“钩戟利刃森森然”的线条,而是唐代以来“弯弧挺刃”、“其势环转”、“勾绰纵掣”的笔法了。“这样的画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三、四世纪晋、十六国时代的作品。斯坦因所以这样往上推,是为了把这作品的题材附会到爱罗神上去。”(注:阎文儒:《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米兰)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载《现代佛学》1962年第5期。)所以阎文儒把米兰这些出土美术品断代为五代至宋初。
关于有翼神像的题材,阎文儒先生认为应从佛教艺术中去寻找,也就是要从印度、犍陀罗与西域各地的艺术中去寻找。接着他举出日本流传的唐舞中的迦陵频舞(即迦陵频伽,妙音鸟之意),与库车和敦煌石窟中有翼舞人及“有翼天使”绘画十分相似。唐代虽然没有流传下来“迦陵频舞”,但是《霓裳羽衣舞》或者就是由这种舞蹈加以改造的。因此推想,“斯坦因所发现的有翼神像,如果不是如马夏尔所提出的‘乾提(达)婆’像,就很可能是唐代以来从天竺传入、在佛教法会前表演的一组‘迦陵频舞’,而不是希腊的爱罗神像。”(注:阎文儒:《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米兰)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载《现代佛学》1962年第5期。)
霍旭初、赵莉的文章明确提出,斯坦因“有翼天使”之说和“有翼天使”代表乾达婆即飞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佛教是个禁爱欲的宗教。如果把“有翼天使”说成源于“爱罗神”,那就成了“爱”的精神化身,把“爱神”引进佛教是违反佛教精神和教义的,因而不能成立。“有翼天使”也不是乾达婆,乾达婆是佛教的八部护法神之一,属于“天部”。米兰佛寺的有翅人物均在佛塔环形护壁下方,这个位置不是表现“天部”的位置,因而画的绝非是飞天。
霍、赵二人把米兰有翅人物与库车昭怙厘佛寺出土舍利盒的盒盖上四身有翅裸童比较,二者完全相同。经过论述,认为上述二者均为迦陵频伽。(注: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与阎文儒关于“有翼神像”的结论相一致。

三
关于米兰佛寺“有翼天使”的不同意见,概括起来争论的焦点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有翼天使”还是汉代画像石中“飞人”或“迦陵频舞”;其二,绘画内容来自印度佛教故事还是希腊神话;其三,绘画产生的时代是三、四世纪还是五代至宋初即10世纪上半叶。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确定期坦因所发现“有翼天使”产生的时代背景。
斯坦因把“有翼天使”及米兰出土相关绘画产生的朝代定为三至四世纪,其根据之一是在绘画上和另外的残绢上发现了佉卢文,与通用佉卢文的尼雅地区所处年代一致相同,也是三、四世纪,这个时期的尼雅(精绝)一直是鄯善国的西境。根据之二是斯坦因在米兰佛寺的一尊坐佛底部,发现了一片用婆罗迷字母写的梵文贝叶书,从这片写于印度的贝叶书上的婆罗迷文字来看,年代最迟不超过四世纪。
另外,沈福伟认为“有翼天使”绘画时代早于三、四世纪,应产生于2世纪。(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著名佉卢文研究专家林梅村则把“有翼天使”产生的时间定在2世纪末至4世纪。(注: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米兰佛寺既然废弃于三、四世纪,那么“有翼天使”产生于2世纪不迟于3世纪,是可以成立的。因此,阎文儒先生仅根据绘画特点,将“有翼神像”的年代定在五代至宋初即10世纪中叶,就没有支持的根据了。当然,所谓“有翼神像”的绘画特点是唐代笔法的观点也就无法确立了。
邱陵《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研究》一文,也认为“有翼天使”完成的时代以“公元2世纪这个年代是可以成立的”。(注:邱陵:《米兰佛寺“有翼天便”壁画研究》,载《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由此可以证明,阎文儒等先生以唐代“迦陵频舞”比附晋、南北朝朝代的“有翼天使”,就很难说明问题了。况且,既使把晚了数世纪的“迦陵频舞”与“有翼天使”相比,其脸形、服饰、风格也很少能找到相似之处。至于说唐代《霓裳羽衣舞》就是由“迦陵频舞”演变而来的说法,就更难令人信服,因为此“羽衣舞”非彼“羽人舞”,查遍有关《霓裳羽衣舞》的各类记载,也没有“有翼”之说,而是因舞者衣上缀满羽毛,或指舞衣轻薄如蝉羽故得其名,与“有翅”形象没有关系。还有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见于汉代画像石)来解释“有翼天使”,这类说法就显得可能过于离奇了。
霍旭初、赵莉不同意斯坦因把“有翼天使”说成是佛教中的乾达婆即飞天,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有翼天使”比较接近西方观念,“它的身份更像西方的天使,而与佛教世界的乾闼婆和飞天距离较远。”(注: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所以斯坦因把二者拉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但也不能因此又把它与“迦陵频舞”甚至《霓裳羽衣舞》联系起来。
“有翼天使”及米兰出土的相关绘画,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具有明显的希腊、罗马风格,与犍陀罗艺术如出一辙,呈现出“古典艺术的灵光”。这些绘画明暗对比法的运用,与犍陀罗艺术中的透视法非常相似。如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所说:“米兰绘画证明在其绘画发展上留有明显印迹的相当复杂和修饰性的透视画法技巧传入了中亚。”(注:(意)马里奥·布萨格里《中亚绘画》。载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34页。)米兰绘画不仅接受了犍陀罗艺术的光色、明暗等技法,而且吸收了以希腊、罗马式为特征的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和观念。印度学者B·N·普里说:“米兰的壁画因其风格的强烈,佛教内容、象征性的结构和贵霜—伊朗式的花边而形成了犍陀罗派主流地区中最为广泛的一支。据推测,米兰这一支已被移植到绘画方面,或者换句话说,米兰艺术已经被当作犍陀罗艺术的一个前哨,表明中亚各民族和贵霜帝国人民之间的接触。鉴于其风格,它们富于西方成份的肖像画法得以极好的重新改造。和众多的绘画比较起来,米兰绘画也许显得普普通通,但谈到佛教绘画,它们的重要性揭示出西方对东方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作为佛教艺术较早的例子,米兰绘画并不是表现出其新生,而是一种进化和相当成熟技巧的产物。”(注:(印度)B·N·普里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佛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363—364页。)诚如以上所说,米兰绘画风格与贵霜王朝的接触和影响有关,这也就决定了“有翼天使”等绘画的西方化色彩。
“有翼天使”那圆圆的睁得大大的灵活而有神的眼睛,嘴唇微合而鼻子修长、鼻头略有钩状,光头上留有发髻而非毛桃形,身着浅圆领套头衣衫的形貌,以及光与影和凹凸法造成的立体效果等等,都体现了鲜明的希腊式犍陀罗艺术风格。
由于当时米兰社会的特殊背景,形成当地文化与贵霜王朝带来的希腊、罗马文化混合并存的状况,加之这些绘画的作者本身就是罗马人或其后裔,因此绘画技巧及文化观念的西方化是完全可能的。“有翼天使”在西方人心目中不是神像,所以其位置处于佛寺走廊稍下的护壁板上且不带背光是符合实际的。“天使”炯炯有神的目光略微仰视,正好与所有经过回廊的礼拜者的目光对视和交流,所以位置是合适的。况且,佛寺内主壁画是佛教本生故事,“有翼天使”只不过是一些起美丽的装饰而已。由于“有翼天使”及相关绘画是希腊式佛教艺术,虽然题材是佛教内容,但其表现形式和手法却是希腊古典作风。因此,米兰画师是采用古代罗马绘画技法并借用希腊神话上的形象来表现佛教内容。“大体可以认定,米兰佛寺中的有翼天使正是古希腊宗教神话中的著名爱神厄罗斯。”(注:邱陵:《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研究》,载《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一推断,是以米兰绘画所处的时代及其特殊的人文背景,为其根据的。
从西方神话上寻求相应的形象,象征性地宣传佛教教义,这是佛教传入不久米兰画家驾熟就轻的一种选择。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形形色色佛教人物形象的形成、变异和确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因此米兰画家佛教艺术希腊化的倾向,就成为佛教东传初始时期的自然现象了。
四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的结果之一,就是埃及、波斯及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化。征服者所到之处,必然带来自己的文化艺术和社会观念。犍陀罗佛教艺术正是吸收了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建立起来的。因此,所谓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式或带有希腊文化色彩的佛教艺术。
犍陀罗艺术发生期,也正是贵霜王朝的活跃期。“贵霜王朝的一个继承人迦腻色伽是一位伟大的君主,被称为犍陀罗之王。其首府在布路沙布逻,即今白沙瓦。他的统治范围从中亚一直延伸到孟加拉。他信奉了佛教,是一个虔诚狂热的佛教徒,有阿育王第二之称。他和同时代的罗马政权关系很好。当时,罗马政权统治着整个西亚。由于这种关系,可以获取罗马的影响以及那里的艺术家,以促进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展。”(注:(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页。)犍陀罗艺术所受的影响不是纯希腊的,而是希腊和罗马的双重影响。
迦腻色伽死后,贵霜王朝出现内乱,在政治和佛教的残酷斗争中,一部分失败者、被排挤者可能被迫出走,流落到于阗和鄯善。至东汉末期,贵霜移民对鄯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佉卢文的流通和佛教艺术两个方面。佛寺以佛塔为中心的建筑艺术、具有犍陀罗风格的绘画、雕塑、家具、装饰品、图案纹样等,反映出大量贵霜移民在鄯善生活的痕迹。“佛教和佛教艺术在鄯善流行和发展,主要是与贵霜衰亡后相当一部分贵霜人流落到鄯善的情况是密不可分的。”(注:孟凡人:《贵霜统治鄯善说纯属虚构》,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上述壁画中的白象身上的佉卢文题记,意为“此画系提塔(Tita)之作品,彼为之获般摩伽钱三千。”(注:林梅村:《贵霜大月氏流寓中国考》,载《敦煌吐鲁番学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斯坦因说Tita很可能是罗马人名Tiuas(提塔斯)随俗语变化了的对应译名。此画家看来不可能是罗马人或希腊人,而应该是希腊化了的犍陀罗人(贵霜)人。“有翼天使”及米兰出土相关绘画,很可能出自画家“提塔”一人之手,或者说有一个画家小组在米兰和周围的尼雅等地的佛教寺院活动,因为他们表现出相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的古典风格,不仅在人物衣饰的处理上熟练地运用明暗对比手法,而且在肖像画法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征。
以上数次提到的白色神象图,是一幅须大孥太子本生故事画,是说叶波国太子须大孥将白象布施于人的故事。太子、白象和景物基本上是写实画法,那光与影的变化对比,显示出西画的特色。
另外一幅在须大孥太子本生故事下面,是由一条波浪形彩环连系着的男女青年群像饰带。这是一组半身人像,或欢愉持重的男子,或美貌盛妆的女郎,有的手持酒樽酒杯(或似长颈瓶和高脚盘),有的捧着乐器,装束不同,神态各异。他们的面容首饰、服装打扮、手中物件,无不显示出浓郁的希腊、罗马式的犍陀罗艺术风貌。
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佛陀和六弟子图的残片。佛陀有背光,右手托起掌心向外,似作施无畏印。六个弟子分两列随其身后,个个都与佛陀一样睁着眼睛。从图中看得清楚,无论那大而直视的眼睛、衣褶和人身的光影对比画法,特别是脸部用轮廓线清晰的勾勒,都使人联想起古典绘画风格。虽然表现的是佛教内容,但其色调、神韵乃至绘画方法、技巧,毫无疑问都是犍陀罗模式。
“有翼天使”及米兰出土相关绘画,无疑都是佛教题材,但表现形式却无一例外采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这一现象,是这一地区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鄯善国的居民是多民族混合型的,有当地土著民族,有中原汉人,也有不少是从印度犍陀罗流入的移民。这里奉行的是一种具有犍陀罗特点的佛教,其艺术特征也必然是犍陀罗的。正如克林凯特所说:“在米兰的佛教艺术中,之所以有明显的西方因素,根源在于:鄯善国是混合型文化,其中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传统同时并存,而看不到人们特别致力于把外来事物披上本地的外衣。但印度却是这样。新疆与南亚和东亚不同,它曾经让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以及生活方式同时并存,而不是立即把这些不同的事物,融合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这一点也反映在使用各种不同文字上。”(注:(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诚然,这种混合型艺术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相互交流融汇的过程,外来因素只能作为本地主体艺术的一种成份、一个补充而被吸收,形成地域民族本身特有的艺术个性。但是,米兰与龟兹、于阗、高昌等地的情况不同。这里的佛教由于不甚明了的情况而中断,尚没有来得及以当地文化为主体对外来的移民文化—犍陀罗文化进行吸收、融化而形成新型文化。佛教文化在米兰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正是贵霜文化在米兰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甚至寺庙的绘画,都是由犍陀罗(贵霜)具有希腊、罗马血统的人一手包办,因此,米兰佛教艺术借用希腊神话里的爱罗神—“有翼天使”来装饰佛教寺院的墙壁。虽然如霍、赵二人所说,把爱神引进佛教是违反佛教精神和教义的,佛教的教义里始终也没有为“爱欲”开过大门,佛教艺术造像从来也没有爱神的地位。(注: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但深受希腊、罗马文化熏陶的画家“提塔”等人,处在有贵霜移民文化背景的特殊时期,加之佛教传入鄯善的历史不算太长,所以把“有翼天使”引进佛教艺术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一历史事实,也是用通常规范的佛教仪轨所难以纠正的。
当然,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和有取舍的。无论多么发达的文化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不能成为另一地区民族文化的主体。即使出现这种文化入主的现象,那也只能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况且,鄯善并没有出现贵霜移民集团,更没有出现贵霜势力统治鄯善的局面。事实上,就是在当时普遍使用佉卢文的时候,汉文仍在鄯善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发挥着作用。同样,米兰寺院佛教艺术出现“有翼天使”和犍陀罗风格的绘画雕塑,适应了贵霜移民及其中的知识阶层的审美需求。但鄯善土著居民和中原汉族屯田将士及其家属,所占人口比重也很大,这就使米兰的佛教艺术中也显现出中原汉地的成份。就是斯坦因本人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承认因为西方艺术经过中间的过程,“当然受有东方观念的影响”。充分显示了两种文化的撞击,并存在着交汇、扬弃、融合和创造新型地域文化的可能性。
公元2世纪至4世纪,米兰出现的“有翼天使”及其他犍陀罗风格的佛教艺术,是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交流的产物,也是中华文化博大包容性的一个实证。今天我们面对这一历史现象,为我们的祖先如此恢宏的开放胸怀和接纳气度,会产生更深的感佩和敬意。
欢迎投稿:307187592@qq.com news@fjdh.com
QQ:437786417 307187592 在线投稿
2.佛教导航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佛教导航将优先发布高质量的稿件,如果有必要,在不破坏关键事实和中心思想的前提下,佛教导航将会对原始稿件做适当润色和修饰,并主动联系作者确认修改稿后,才会正式发布。如果作者希望披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和个人简单背景资料,佛教导航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3.文章来源注明“佛教导航”的文章,为本站编辑组原创文章,其版权归佛教导航所有。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来源“佛教导航”或作者“佛教导航”。



